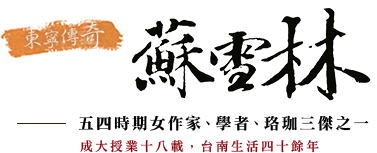
蘇雪林教授小記 公孫嬿
劉朗學長轉達厲師厂(?)樵之命,囑我寫一篇文章,介紹蘇教授雪林姑母。在中國文壇上,蘇教授的聲譽和地位,用不著我來畫蛇添足的多說一些什麼,凡是對於文學稍有興趣的老年、中年、乃至於少年人,沒有一個不對她老人家敬佩與稔熟的。現在我只記幾件小事,來看看她的性格和人格。也許我的筆鋒遲鈍,不能狀其萬一;但是我相信時間是最好的證人,她四十年來的奮鬥,和她為人處世所閃耀出的光輝,以及嫉惡如仇的果敢態度,終久有一天會照爍歷史的。
蘇先生雖然寫了幾十年的文章,但是直到今天她下筆的慎重,和對詞句的推敲勘酌,其態度之嚴肅,我還未見有能出其右者。四十二年我在臺灣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海的十年祭》請她寫序,那時我正在臺南砲兵學校受訓,她在師範學院執教。序寫好了寄我看,我真是受寵若驚。同時她告訴我:「這序可能引起別人的反感,認為我把你捧得過火。我準備承當一切的責難,希望你更加努力不負我的期望。」首先她這勇邁的作風,就讓我感激得落淚;以後我才知道她並非對我如此,對於所有的後進,她都願盡力的提挈和鼓勵,有時也毫不客氣的指責。就在奉到序文的三天之內,又接到她百忙中寫來的兩封信,原來其中有某一個字不妥,或某一個標點符號不對,她的信就是更正這些的。最後,她讓我重抄一份寄回,她還要刪改,等這篇序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我打算把它交給出版公司排印之前,她還修正了一次,才成為定稿。
四十三年中央文物供應社預備為我出版兩個集子──一本是詩集《大兵謠》,一本是短篇小說集《孟良崮的風雲》。當時我不在臺北,野戰部隊生活是動盪的,我想起在出版《海的十年祭》之前,那三篇文章請蘇先生教正時,她曾逐句看過,不僅給稿上加了眉批,凡字句不妥之處,也經用紅筆改好,我只得再麻煩她老人家一次,把原稿一束呈上,並請代我校對。等兩本書都付梓了,我才有機會到臺北師院教職員宿舍去看她老人家。她幾乎是咆哮的問我:「看你這兩本書真吃力,比我自己寫都累。為什麼其中標點符號錯了那麼多?難道你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嗎?措辭用字我都替你考慮過了,如果這樣潦草的拿給張先生,怎麼對得起人家對你的栽培?為什麼你自己不多看兩遍呢?以後你寫文章再這麼粗心大意就不行,得打稿練習!」我唯唯遵命,這以後影響到我五年來創作的態度。提起筆彷彿她憤怒的責難就在耳邊。我知道,這是她對我希望過高,因之責備愈為深切的緣故。
四十二年秋,我幸運的調防駐紮在淡水,當砲兵連長,自已有部吉甫車,每逢假期我就開車到臺北,向蘇先生請教的機會多了。時常聽她對我的訓誨,使我堅定了一個信念──便是天下絕對沒有來之物,想成功一點事業,非付出血淚汗的代價不可。我們只曉得蘇先生民國十年留學法國,十八年出版《棘心》震動文壇,但是忽略了她的刻苦奮鬥的精神。由《棘心》中,我們還能捉摸到一些當年她老人家和環境,和社會,乃至於和那個時代思想交鋒對刃的痕跡,而今天蘇先生已是將近六十歲的人了。我更忘不了的是夏夜在師院宿舍中,蘇先生為我講述《楚辭》和〈九歌〉的情形。講得高興時,她跑到書架上,取下一大本一大本的各國原版書籍,按照著圖像,證明她正確的見解。我記得有一晚談到〈九歌〉中的大司命和《山海經》,她老人家竟天真的笑了起來。
那年過舊曆年,她特意寄來了一封信,囑我陪她過年,因為我那位表弟不在臺北,借的地方是她一位親戚的客廳,年夜飯我沒有趕上吃,去時看到她老人家穿了一身黑絲絨的長袍,戴上手飾,像參加盛典似的。還有主人和那位太太,我們海闊天空的談著,當然還是脫離不了文學的圈子。她一再的將盤中糖果抓給我吃,並且看著我吃小點心和餅乾。那情景使我想起淪陷在大陸的母親,也記起在二十七年前母親看《棘心》時對我說過的話:「這本書好極了,是你蘇家姑姑寫的,你要好好看!」誰料到這便是我從事新文藝習作的一本啟蒙書,考入天津南開中學之後,我還把它送到書肆中重新裝訂過。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在臺灣見到蘇先生,我已然由少年步入中年了。
當我奉命開到金門前線時,對我鼓勵最大的,也是我的表姑蘇先生。駐在烈嶼最前線,幾乎每日不停的砲戰,她給我寄來的書和信,都使我在砲戰之暇的有生之年,不敢忘記這枝筆,我練習寫作,用許多不成熟的文章安慰老人家的心。直到她慨然的說:「這幾年來任多事者攻訐,我不求別人的諒解,我只希望事實肅清讕言,你的努力已小有成就,證明了我老眼無花。」我告訴老人家的是:「嫉妬和無的放矢,也可以鼓勵人發人猛省,我覺得非常對不起姑母,您對我的慈愛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我但願將來在事業上─不論是文壇還是戰場─能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作為,俾盡侄兒這一片誠摯的孝意。」將來看機會,我很想把三年來在前線上準備犧性成仁前,和姑母和朋友們來往的信札整理一下;讓世人曉得,在大時代中一個人想屹立不倒,應俱有那些種力量來支持。
我確認蘇先生的作品,適合青年和軍中閱讀,她反共的思想積極,而是非善惡之感尤重。在當年留法的時候,便受左翼匪徒的詆毀,今天她能安心的在臺灣研究屈賦作學術界的中流砥柱,是有長久的淵源的。我在前線接到的她每一封信,都是義正辭嚴、大義凜然。她的道德觀念,即使不和她接近,也能由她的文章中體會到。我沒有看到比她更淳樸更謙虛的人,如為了慎重,在草擬這篇小文之前,我曾專函到臺南成功大學徵求她的同意她卻回信說:「《筆匯》要介紹作家,第一個不必是我。我對於這件事非常厭倦,因為文壇進步一日千里,像我們老一輩人久已落伍了。還提他做甚?而且我平生創作純文藝極少,只算個『文壇打雜』,《筆匯》雖不嫌我資格不和,但我實自知其不配也。所以你可以請他們先介紹別人,經過幾個人之後,再輪到我亦可,但我希望他們能放我安靜。」
雖然未經姑母的同意,我總算是先備案了,如今不放她安靜的卻是我,這是我要深致歉意的。
(四月四日夜草)
原刊民國四十七年筆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