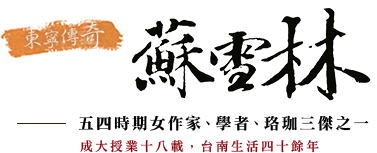
那「坐忘」的身影 唐亦男
有時且不惜編造美麗的謊言,來欺騙自己、安慰自己,在苦杯之中攙和若干滴蜜汁。但她本人早已揚棄了這類自稱為「幼稚浮淺的作品」。
如今她已九十多歲,跨越了兩個世紀,無論學問智慧,或經驗閱歷早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我們很希望看到她的本來面目,讀到她的心路歷程,去掉文學作品中的「馬雅面紗」,歸真返樸,寫一本翔實的傳記,並有熱心的歷史系同仁建議,何不用「口述歷史」的方式,由她敘述錄音,然後由學生來筆記整理,但是蘇老師要求嚴格,形諸筆墨的事,絕不敢假手於人,迫不得已,才由她自己來寫,這就是最近由三民書局出版的「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迫不得已的另一原因,即成大中文系與武大校友會,在四月十一、十二兩天,要為蘇老師九十五歲生日舉辦一次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到二十多位與她創作研究相關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評論她的著作,這應該是對一個學者最大的尊重與敬意,讓世人知道她投注畢生心血努力研究的成果與貢獻。
當時徵求蘇先生同意的時候,她一直不肯答應,而且說一個人到了她這樣的年齡,只求圖個清靜、無榮無辱、翛然物外,如今卻要勞師動眾,為她個人舉辦什麼學術研討會,那是萬萬不可以的。但是我一直勉強她說:您一生孜孜不倦研究學問,不就是希望有人了解您做出的成績嗎?即使不為自己,也要為您發現的治學方法、學問內容,讓更多人能分享您研究的成果。您發現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為中國文化爭得「文化冢子」的地位;重新建構諸神世界,肯定民間文化的價值,並找出楚辭屈賦研究的新路線,還有多種有關歷史上、學術上的新發現新考證,怎麼可以不為人知呢?
我還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如她研究屈賦,得到了一個「一以貫之」的方法,能夠把中國甚至世界文化中許多雜亂無章的文化份子整理成一種井然有序的系統,而這一方法是她從搜討域外古代的宗教神話和其文化份子之後無意中得來的。當然不為那些只知道從故紙堆中尋找答案的老先生們所認同,他們堅持自己的看法為「正法眼藏」,而她的發現是「野狐外道」,這一判定顯然刺激了她,使她決心要在有生之年將兩千多年來無人獲得正確答案的屈賦之謎揭穿。
又蘇老師不僅在新舊文學方面造詣頗深,創作方面更是才華洋溢,被譽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但是她卻視文學為「雕蟲小技」,自稱「從開始寫文章時,便不想做一個文學家,若說我薄文學家而不為,也未嘗不可以。我是歡喜學術的,只想在學術上有所成就。」雖然學術研究枯燥生澀,極端乏味,但她卻在這方面享受到比創作更大的滿足;因為她做學問,有一種獨得之祕,喜歡另闢蹊徑,發現前人所不能發現的問題;常能索隱鈎沉,解決前人積疑已久的懸案,故又被稱為「文壇名探」。但是一般人往往忽略她這方面的成就,推崇她讚美她的永遠只限於早期發表的那幾本小說散文。雖然她並不灰心,說今天不為人知,五十年、一百年之後,總會有人知,甚至如莊子所謂:「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但因此亦證明懂得欣賞文學的人遠比懂得學問的多,而她的散文之美又遠超過考據的枯澀吧!
蘇先生還在文章中說過人類的「是非心」「正義感」「真理愛」,都是與生俱來的,而這些在她的性格中表現尤其強烈。無論對人對事,她都要辨明其是非曲直,然後嚴加褒貶,用辭直接銳利,有如春秋之筆;加上好善惡惡的性格,敢愛敢恨,敢說敢當,因此得罪不少「文壇名人」,也為自己招來種種奇恥大辱,她說如果不是有一種天生的木瓜氣質,發生了抗毒作用,說不定早已羞憤自殺了。
除了不了解她的性格學問一面,更不了解的是她現實為人一面,例如很多去訪問蘇先生的人,對她居住的簡陋,生活的清苦,總是十分不忍。幾個月前,還有一位被稱為女強人的作家到臺南演講,特別抽空去拜訪她口中的「愛國的學者,其文學上的成就,已是各界公認國寶級的人物。」當她看到蘇先生客廳破舊的傢具,桌上剩餘的飯菜,頓起惻隱之心,對蘇先生這種「窮苦、潦倒,三餐不繼」的現象,以及到老「還得靠爬格子賺錢貼補,境況堪憐」發出不平之鳴,並不滿成大對待老教授的方式:「聽說成大正籌劃在明年四月召開國際學術會議,專門討論蘇教授的專述,屆時勢必要花上一筆經費,既然如此,現在為什麼不好好照顧她的生活?」這一呼籲見報之後,嚇得蘇先生趕緊投書到報社解釋,除了表示「對貴報十二版有文學國寶級人物蘇雪林,晚年窮苦潦倒,三餐不繼,朱秀娟擬申請為大師募捐不勝駭異」之外,並說明「本人喜撰寫少許雜文,無非資以消遣,並非煮字療飢……再者,本人民國六十二年起由成大退休即借住成大教職員宿舍至今。蒙學校方面多方照顧,無微不至,本人已銘感萬分,安可再請額外之惠,某某所請固出於愛我之厚意,然實際上皆不必也。」(以上具見八月十、十一日之臺灣新聞報)該作家萬萬想不到她的一番善意的同情,所引起的後遺症,不僅對一位狷介的老教授其人格尊嚴受到了傷害,還有經報紙一傳播,社會上的善心人士及救濟機構的捐款,有的一千、有的兩千,或寄到蘇先生家、或寄由成大中文系轉,光為了寄還這些捐款,及婉謝信函,就不知增加了多少困擾,蘇先生是又煩又氣,直說「害死我也」。
我從大三選修蘇老師所開的楚辭課,畢業之後又有幸與老師同在成大教書,同用一間研究室,同住在一條東寧路上。掐指算來足足有三十八個年頭,雖說魯鈍,智不足以知吾師,但卻能做到「污,不至阿其所好」,在我的眼裡,她早已達到了莊子所說的「吾喪我」的境界,因為她有兩個我:一個是現實中的我,一個是創作中的我,只有在研究創作中,她的生命才是真實的、煥發的。她描述自己研究屈賦那種渾然忘我的境界說:「我整個身心沉浸于這項靈感裡,足足有十天之久,彼時胃口完全失去,睡眠時身雖偃息在床,心靈則清清朗朗醒著,我那個靈感像一顆晶瑩透澈的大珠寶,發射出閃爍的光芒,照徹我靈臺方寸之地,不,竟可說照徹了中國幾千年的故紙堆,一直照到巴比倫、亞述、埃及、波斯、印度、希臘等國的古代史。……那時我的智力活動,達于最高峰,好像佛家所說,一個過來人遊歷前身曾遊之境,當其宿因頓悟,便一切恍然,某闥某房,叩關直入。毫無疑誤;也好像當年屈大夫的英靈,降臨到我身邊,冥冥中指點著我。他打著光明的火在前引導,我的心靈則上天下地,跟隨著他到處飛翔。我的目標倘在幾千丈的高峰之上呢,我並不必逐級攀登,卻從空直落;我的目標倘在萬里以外呢,也不必渡水登山,按驛前進,只須振翅一飛,便飛過前頭去了。」《談寫作的樂趣》)
尤其四年前老師跌斷左腿,不良於行以後,我每次推門進去,她不是坐在籐椅上看書看報,就是坐在書桌旁伏案疾書,我想這豈不是莊子所描述的「坐忘」嗎?她不但忘記了吃好的穿好的,室內的擺設,室外的景觀也早已不再留意,除了學問,實際上生死也早已相忘。她所念茲在茲的是她的屈賦研究,她說:「我於無意之間發現探討屈賦的新路線,興奮之情使精神變成白熱燃燒的狀態,對於這個研究簡直愛得如醉如癡,好像為它犧牲性命也心甘情願」。她的痛苦也是來自研究的不順利,她說:「當我的這個研究不能順利進行,或進行時遭遇盤根錯節難題不能解決,我的痛苦之大是無法形容的。我覺得像屈賦這樣一個大題目,不僅關係整個中國文化,並且牽一髮而動全世界,以我學問的淺陋,能力的薄弱,想挑起這份重擔,多少是有點妄想,況我年齒已暮,設一旦溘先朝露,則這個絕大秘密亦將隨我永埋白楊黃土之間,那我不但對不起自己,也對不住屈大夫的英靈,更對不住學術界了。」今天她的屈賦研究早已完成,對學術文化的神聖使命也已盡心盡力,但是她仍舊鍥而不舍,不知老之將至的在學術的園地耕耘,不斷有收穫有發現。她說:「當你研究一項學術,忽然發現了一條從前任何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你循此路向前走去,忽然有個莊嚴的燦爛世界展開在你面前」。而她就沉浸這樣奇妙的世界中,「早已忘記了疲勞,疾病,使我無視於困厄的環境,鼓舞著我一直追求下去,其樂真所謂南面王不易。」(以上引自蘇雪林自選集)顯然她已將身心化入學問中,享受到南面王不易的最大樂趣。
近十多年來,隨著臺灣經濟起飛,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著提昇,物質享受更是充足富裕,對於老一輩讀書人固窮的執著,以及淡泊寧靜的生活已不太能夠了解;用莊子的話就是現代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要他們去體會精神生活中的忘我境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難怪蘇先生的晚境不但「孤獨」,而且真的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