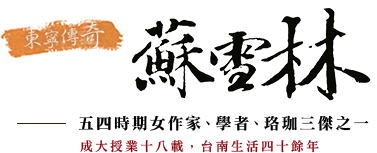
 永遠的梧桐 馬森
永遠的梧桐 馬森
在我幼年的心裡,覺得這位女士模樣應該像在電影裏出現的神秘貴婦,是遙
不可及的,誰知人事難以預期,多年後竟坐在教室裏聽她講解「楚辭」……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這樣惋惜地說。
這是蘇雪林老師〈禿的梧桐〉一文中的前兩句話。幼年時在課本中讀到,印象特別深刻。後來讀過的一些文藻華美、學問淵博的宏文,倒都忘懷了,唯獨淺白如〈禿的梧桐〉或朱自清的〈背影〉,反而永駐心頭,歷久難忘。足見淺白的散文,正如簡易的詩篇,常可直入肺腑,具有深鐫心版的藝術魅力!
後來又讀了《綠天》一書中其他篇章,都覺得委婉纏綿,餘音嬝嬝。《綠天》的作者好像用的是綠漪女士的筆名。在我幼年的心裡,覺得這位綠漪女士模樣應該像在電影裡出現的神秘貴婦,是遙不可及的,誰知人事難以預期,多年後竟坐在教室裡聽她講解《楚辭》。
大概是民國四十年吧!上大二的時候,開學後突然了一位教《楚辭》的新老師,清瘦的身材,白淨的面容略帶一些倦意,說話時聲音細緻婉轉,有些喃喃自語的味道。她就是我們久已聞名的女作家蘇雪林女士,那時剛從海外歸來,被師院(國立師大改制以前)的院長劉真先生捷足先登地聘為國文系的教授。那時候我們國文系的教授陣容可說是一時之選:教詩詞的是高明先生、教訓詁學的是潘重規先生、教諸子和理則學的是牟宗三先生、教甲骨文的是董作賓先生、教鐘鼎文的是高鴻縉先生、教聲韻學和文法的是許世瑛先生(許壽裳先生的長公子)、教詩經的是屈萬里先生、教莊子校勘的是王叔珉先生、教文學史的是李辰冬先生、教新文藝習作的是謝冰瑩先生、教修辭學的是趙友培先生……好像正好沒有教《楚辭》專家,蘇雪林老師的適時而至,可以說填補了這個空隙。
蘇老師上課從不抬頭看學生,因此我想她不多麼認識我們。如果學生不去主動找她,她也不會主動地找學生。她是那種深居簡出,不喜歡交際應酬,一心專注於寫作研究的學人,所以一生才會完成數十部學術創作兼備的著作。她對學生的態度從來都是從容溫和,沒有聽她疾言厲色地說過話,更不要說是發脾氣了。
忘記是聽蘇老師說過,還是看過她一篇在法國採葡萄的文章,使我在大學時期一直嚮往法國葡萄園的風光。想像在晴朗的藍色天空下,一望無際的綠色藤蔓,錯落著隱覆在綠葉下的串串晶瑩的紫色漿果,耳中似乎迴響起採果的青年男女爽朗的笑聲,口中竟彷彿溢出了酸甜的美味。後來我自己在法國住了七年之久,可惜因為工作、研究兩忙的緣故,竟始終沒有能夠兌現這個久存心底的採葡萄的夢想。
大學畢業後到外地教書,很久沒有再見過蘇老師。但是在研究所的時候卻又見過幾次。一天,忽然心血來潮,想到了久未見面的蘇老師,便騎了腳踏車到她住的那間簡陋的紅磚教職員宿舍向她問候。一見面,蘇老師非常高興,問長問短,自然,她並叫不出我的名字。過了一會兒,她才躊躇地說道正有一筆稿費好久沒能去領,因為自己身體不好,出門不太方便。聽了,我便立刻騎車去替她領回來。又一次是蘇老師跟師大的一群學生同遊金瓜石,那次我也參加了。一路上我和另一位同學在她老人家爬上爬下的時候擔任她的扶手和拐杖。我現在還保留了一張和那位同學從山坡上一邊一個把蘇老師架下來的鏡頭。
為蘇老師做的另一件讓她開心的事,是在我擔任「聯合文學」總編輯的時候,為她在「聯合文學」出了一個專輯。其中有張曉風女士寫的一篇詳盡的專訪、秦賢次先生編的「蘇雪林先生著譯書目四十種」和蘇老師自己撰寫的文章。也為她拍了不少生活照片。那一年,她已經九十二歲了。
蘇雪林老師生於一八九六年,年輕時經過了民國的建立和五四運動,屬於第一代的中國新文學作家。那一代的作家,如今多半都已花果飄零,蘇老師和大陸上的冰心女士、巴金先生,是少數幾位碩果僅存的長者了。這次我們為慶祝她九五華誕,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意義真是不同凡響:一者是我們這群受教於她的學生們感念她一生不懈的教學精神和豐碩的研究成果,二者也是為紀念五四一代的作家們為中國和新文學開路的功績。
五四的一代雖然就要過去了,但正如蘇老師在「禿的梧桐」中所說:「我知道有落在土裡的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