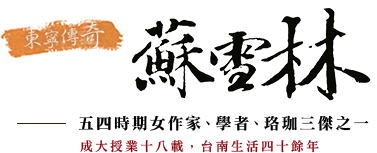
玲瓏剔透的瓔珞──蘇雪林著《綠天》讀後感 錢歌川
約莫三十年前出版的《綠天》,是蘇雪林女士的成名作,洛陽紙貴,風靡一時,作者在臺灣版的序文中也說,「今日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於此二書(《綠天》與《棘心》),殆皆曾經寓目。」而我不瞞你說,卻實在沒有拜讀過,原因是我當時也許不在國內,自然很難得讀國內的出版物的。幸喜這書今日又在臺灣重印出版,而且又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與其說是舊作,不如說是新書更為恰當些,裝幀印刷,都臻上乘,我相信比當年所印的更要漂亮。我在年輕時雖失去第一個欣賞的機會,今日得收之桑榆,細細盥誦,只覺得比從前讀它的人,更有眼福。
作者謙遜地說:「像《綠天》這類久落時代之後的作品,哪有重印的價值呢?」其實文學作品,是沒有時間關係的,只要它具有一種文學價值,千百年之後,還是一樣地要被人誦讀,何況這部《綠天》,不僅文字優美,文學趣味極為濃厚,而且有人間的至情浸潤其中,無法磨滅。〈我們的秋天〉,簡直是一篇篇的散文詩,晶瑩可愛,宜乎他們要選去作為中學的國文教材,給學生們去學習模仿呢。
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是原來《綠天》中的文章,第二輯是遊觀集,第三輯是童話體的劇本與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三者互不相干,勉強湊在一起的,但實際上是很有連貫性的,因為其間有一個中心在。正如作者在序文裡所提示的,這本書的出版是用來紀念她們的珠婚的,雖則三十年來那對她是一場「不愉快的夢」,然而她們始終「維持夫婦關係」,所以到今天才能夠出書紀念她們的珠慶。
以一個文學家和一個工程師結婚,當然志既不同,道亦不合,氣味更不能相投,「新婚最初兩年歲月裡,似乎過得頗為幸福」,那只是因為彼此尚不深知,互存客氣,未完全把本性表露出來的緣故。所以《綠天》(第一輯)裡所表現的,甚為恩愛美滿,〈鴿兒的通信〉也夠情意纏綿,雖則在那第二封信裡,我們就看到了一點不和諧的預兆:「但石頭板著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不理。於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她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辟辟拍拍,溫柔的巴掌,儘打在石頭的頰邊,她(指水)這回不再與石頭鬧著玩,卻真的惱怒了。」在前一文中,我們剛讀到男主人公的名字是石心,而水是代表女性的,《紅樓夢》一書給我們的印象正深,所以現在聽到水石相激的這種玲玲的清響,就使我們不由得要感覺到是象徵著一種勃谿,雖則原意未必如此。
第二輯寫遊觀之樂,原是夫婦同遊的,自然與前輯有一脈相通之處。第三輯是以物擬人,然仍不失為夫子自況,表示出終與愛人分開的一段悲歡離合之情景。尤其是末尾〈銀翅蝴蝶〉一篇,寫得更為明顯,蜜蜂代表那位不懂溫柔的工程師,使得「小小銀翅蝴蝶,仍然是孤獨的。」但她又不願接受別人的愛,她說「我們的婚約,是母親代定的。我愛我的母親,所以也愛他。」當然這種勉強的愛是不能持久的,於是她漸漸感覺不甚協調了,而終至於被「自然的老祖母……把她婚姻簿上應享的幸福一筆勾銷了。」
小小銀翅蝴蝶和蜜蜂分居後,就與她姊姊同住一起,組織「姊妹家庭」,友愛彌篤。春去秋來,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歲月,於是罡風突來,把「繡原」上的花草昆蟲打得七零八落,死傷無算(這當然指的是八年抗日戰爭。)待風勢甫定,大家去收拾殘破的家園,忽又捲起了第二陣大風──赤色蝗蟲的風暴,她姊姊由蝗區逃脫,來到繡原東南邊的一個小小綠島上,她也就從異地飛回到這綠島上來,得和姊姊重新歡聚。大家日夜淬厲,準備反攻。蝴蝶也就一反前此的柔弱,而變得剛強起來,「要做個英勇鬥士」了。
作者對於國家觀念是很深的,我還記得在抗日作戰的時候,她首先把十餘年教書寫作的積蓄換黃金若干兩,悉數捐獻國家,以資抗戰,一時佳話傳遍全國。我們在這本《綠天》裡,也處處可以看出作者強烈的愛國心來。誠如:「只願這一顆瑩潔的明珠,永久鑲嵌在我們可愛的中華民國冠冕上,放著萬道光芒,照射著永不揚波的東海,輝映著五千年聲名文物的光華。」
「我常自命是個自然的孩子」,她又說「大自然的『美』是無盡藏的」。加以她博覽群書,熟識鳥獸草木之名,「時常憧憬於動物的世界裡,所以那形形色色的飛走跂潛之倫,每每充牣於我的筆底」。她喜歡以自然界為背景,尤善於描寫自然界中的生物,以襯出「萬有皆同春」的欣欣景象,更顯得大自然就是一首詩。她對無生物賦予生命,對有生物又給以人格化。她又常透過動物來看人的行為,如〈鴿兒的通信〉裡說的「小公雞被趕得滿園亂飛,一面逃,一面叫喊,嚇得實在可憐,並不想回頭抵抗一下。如果肯抵抗,那白公雞定然要坍臺,牠是絲毛種,極斯文,不是年富力強的小公雞的對手。我於是懂得『積威』兩字的厲害了。」
作者誠不愧為中國文壇的宿將,其詞藻的豊富,和筆致的細膩,目下尚無人能出其右。你如不信,請看下面這段描寫月夜的筆墨:「棧橋兩邊立著兩行白石柱,每一柱頭,安設一盞水月燈,圓圓的正像一輪乍自東方昇起淡黃色的月亮。月亮哪會這麼多?想起了某外國文豪的雋語:林中的煤氣燈,是月亮下的蛋。現在月亮選取東海為牀,將她的蛋一顆一顆自青天落到軟如錦褥的碧波裡。不知被誰將這些月蛋連綴在一起,成了兩排明珠瓔珞,獻上海后的柔胸。海后晚卸殘妝時,將瓔珞隨手向什麼上一掛,無意間卻掛在這隻銀箭上了。」
又作者發現勞山的特點在石,便寫出:「一望滿山滿谷,怪石巑岏,羅列萬千,殊形詭貌,莫可比擬。勉強作譬,則那些石頭的情狀:有如枯株者,有如香菌者,有如磨石者,有如盆盌者,有如覆釜者,有如井闌者,有三五攢剌如解籜之筍者,有含苞吐蕊如妙蓮欲放者。有卓立若寶塔者,有亭亭如高閣者,有翼然如危亭者,有奮翼欲飛如金翅鳥者,有負重輕趨,若渡河之香象者,有作勢相向如將鬥之牛者,有首尾相銜如牧歸之羊群者,有斑斕如虎者,有笨重如熊者,有和南無入定之老僧者,有衣巾飄然如白衣大士者,有甲胄威嚴如戰將者,有端笏秉紳如待漏之朝官者,你有觀音的千眼也不能一一諦觀,你有觀音的千手也不能一一指點。」
你如果想看看作者的自畫像就不妨跟我上西湖一趟,那時你便可看見一位少女的〈芳堤走馬圖〉:「那匹馬毛片是淺栗色,我那天身上穿的恰是一襲淡黃高麗布衫,腰間斜佩著一個綠色帆布旅行袋,一頂寬簷白草帽卸在背後,湖上吹來襲襲的和風,拂亂了我蓬鬆的短髮。在那暖巒浮翠,湖光瀲灔的背景裡,我儼然自命是圖畫中人。」這是她自已也終身低徊詠味、永久珍惜的一日風流的賞心樂事。
從前印度貴族男女,皆綴珠玉以為頸飾,梵語叫枳由羅,中國就說瓔珞,作者便拿來形容長堤上成列的明燈,好像是海后柔胸上掛著的珍珠項練。我讀完這本《綠天》,感到書中美辭麗句,俯拾皆是,也好像玲瓏剔透的瓔珞一般,所以就借用了作者在本書中所使用的詞藻來作文的標題了。作者該不至笑我剽竊吧!
原刊民國四十四年新生報副刊